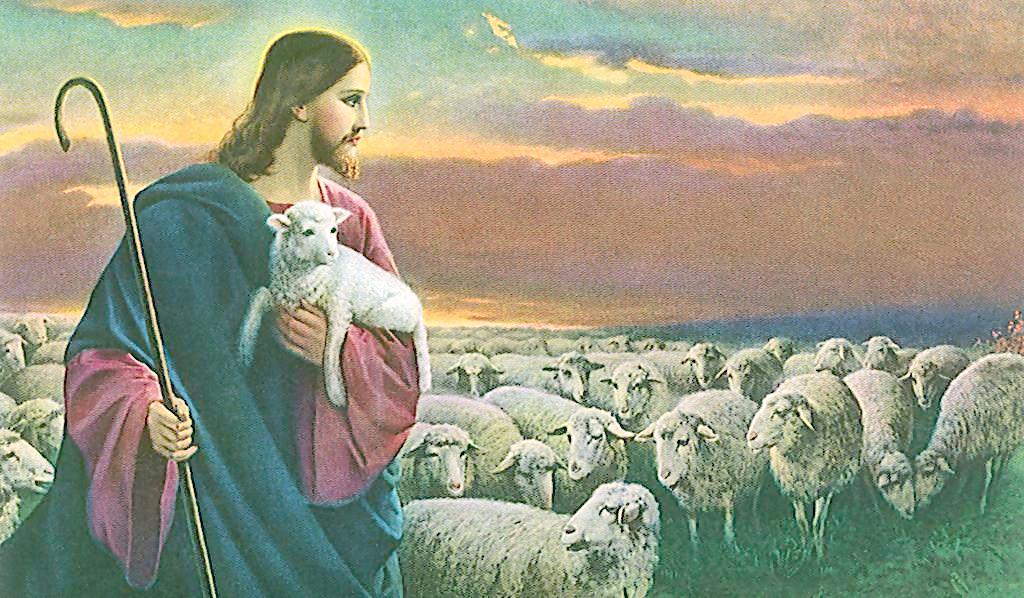|
新闻
国内
海外
社会
祷告 学习 进深 资源 文艺 诗歌 小品 笑话 |
福音
初信
讲章
资料
见证 科学信仰 疑难问答 音乐 小羊 赞美 天韵 |
舞蹈
广播剧
祷告吧
生活 感悟 妙语 心灵 圣经 在线圣经 圣经朗读 |
生活
恩典
亲子
婚姻
讲道 吴勇 宏洁 崇荣 教堂 每日灵粮 恩典365 |
在线祷告
欢迎投稿 在线查经 老版网站 奉献支持 基督书库 |

第二篇第八章:安琪订婚
向安琪求婚后不久,院长郑重地邀约安琪父母谈话。 傍晚时分,孤儿院附近的红房子咖啡屋,他们的谈话进行得很愉快,因为有一共同关心的人成为维系他们彼此情感的纽带。
说到安琪,爸爸妈妈在关爱中掩盖不住操心和忧虑,因为到目前为止,他们心爱的女儿的几大心结依然没有解开,比如:怕绳子,不愿跟任何人谈起十岁以前的经历,还有身上神秘的花斑。 院长听着,喝了一口咖啡,说,至于她身上的花斑,我现在倒有信心控制。要说治愈,可能还不会那么快,但至少,不会往更严重方面发展了。而且这种病需得彻底治疗,否则可能会复发。但不知,她怕绳子和封闭童年生活的心结,是怎么形成的呢?
妈妈也喝了一口咖啡,沉默半晌,看着院长问,她的事,她没有告诉你吗? 院长沉思,摇摇头。 妈妈说, 她自己的事,最好还是由她来告诉你。既然她还没有说,我也就不方便多讲。事实上,对这些问题,我们不比你了解得更多。刚才你说到她身上的花斑,我看你好象还挺了解,能告诉我,这到底是什么病吗?
院长又沉思了,许久,说,我相信她会好的。转而目光落到陈恩珏脸上,关切地问,伯母,您脸色不太好,很黄,身体还好吗?
陈恩珏叹了口气,道,身体呢,反正也就那样子。到了这年纪,要生龙活虎般总不可能。脸色黄呢,是因为我的肾不太好。
院长哦吟一声,转向安琪父亲问,伯父,您那边生意、、、、、?还顺利嘛? 哎,别提了。
雪松杰喷出一口烟雾,在烟灰缸里狠掐了烟头,拿小勺在杯里搅拌搅拌,端起来,晃悠几下,喝一口咖啡,说,都是恶性竞争,整得人根本没法干。你从国外过来,可习惯中国人的做事方式?我是中国人,说实话,我都吃不消了。
呵呵呵,院长眯起眼睛,诡秘地笑说,您的家具店不是在新中一街吗?跟您说实话,那整条街,都是我手下的房产公司修建的。我可以叫市里的工商部门找理由马上吊销您竞争对手的营业执照。
略停顿,问,同意我这样做吗? 雪松杰心里动了动,扬扬眉头没说话,转头看妻子的反应。意料之中,牧师陈恩珏以自己的一贯立场婉言谢绝了院长的好心建议。
院长不自禁竖起大拇指,夸道,佩服啊,有信仰的人还是高尚哪。 妈妈微微叹气,道,哪谈得上高尚?其实,人都是罪人。圣经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
雪松杰蹭蹭妻子胳膊,环顾环顾周遭说,你又想布道了?
呵呵,院长笑说,可以理解,安琪也那样,口口声声说自己是罪人,还要我认罪。伯母,我跟你说实话,我相信真有神,这世界确实太奇妙。但不要总这样悲悲惨惨地把自己定为罪人。人类还是伟大的,你我虽然渺小,但从某种意义来说,还是伟大的,高尚的。
陈恩珏欲作辩驳,雪松杰又蹭蹭她胳膊,说,好了,你别急,允许别人的认识有个过程的嘛。好了,这事今晚就先不提,不提了,谈点别的。
于是他们的话题就从信仰上转开,院长谈到在中国投资上的计划,慈善方面的打算,等等,令雪松杰赞叹不已。
不知觉到了九点半,院长向安琪父母提出最郑重的一件事:向安琪求婚。 雪松杰面露喜色,扭头打量妻子,发现她蹙着眉头,神色严肃,少不得藏起自己的心意,又掏出烟,问院长,来一根?
表情庄重的院长摆摆手推谢,于是他自己点起烟,一副沉思状。
许久,陈恩珏轻咳几声,开口,这个事、、、、、眼光与院长的视线相遇,说,容我们回去商量一下,可好?我们全家会认真斟酌这件事。
他们到家,安琪抱着蓓蒂迎出来。原来,她知道院长晚上找父母求婚去了,料到妈妈必定说回去商量商量,因此下夜课后,她就打车回家了。
一家人坐在客厅,进行一次随意的家庭会议。好久,他们没有开会了。 父母关心了一番安琪的身体状况,人身安全,工作进展等几方面问题,就转入目前最核心和最重要的感情问题。
从安琪自己传递过来的信息看,她已经动心了,而且陷得不浅。但妈妈总觉得,初次恋爱的姑娘容易被感情冲昏头脑,怕是缺少理性思考。她突然想起一问题,问安琪,你审视过自己的感情吗?我记得,你对他已经很有好感的时候,心里却还爱着一个自传中的男孩?
妈妈的问话,仿佛在安琪被柔情蜜意所弥漫的心湖里扔进一块巨石,湖面刹那波涛汹涌,脸上的喜悦瞬间退去,眼神沉郁下去,身体陷进沙发中,深思半晌,说,我不知道,到现在,我依然爱着那男孩。但他可能只是一幻象,是我理想爱情的影子。
那也就是说,院长现在还不是你最心意想要找的男人?要是那男孩出现在你生活中,你会作怎样选择呢?妈妈紧接着问。
这、、、、、安琪慌乱了,眼神迷离,说,其实要说他,倒是什么都好。虽然他现在的信仰、、、、、、、但我很确信,以后他一定会认罪,会归向信仰。我也不知道,是哪点让我感觉他身上缺少。假如那个男孩出现,我想我就不会选择他。
妈妈两手抱在胸前,认真听着,说,那我认为现在你需要冷静几个月,好好审视自己内心的感情。说不定那男孩、、、、、、、话未完,感觉不合适,就收回了后半句。
一直沉默的雪松杰一听,急着接话荏道,牧师太太,我怎么发觉你现在越来越浪漫了。那稿中的男孩,连影子都看不到,怎么可能?这念头就得彻底打消才对。我说啊,孩子的婚姻大事,咱作父母的,就只能作个参谋而已,大头的,还得她自己拿注意。
妈妈扭头,观察安琪的神情,怔住了。
爱情已在她心灵中发芽,在她额头双唇两颊眼睑睛瞳处抽节,仿佛严冬过后,被春风招唤的嫩芽。 但她也清楚地看到,这蠢蠢欲动的苞芽,灵魂中有一份更加的渴慕,是为着春雨的滋润, 妈妈心存忧虑,但同意了女儿的爱情。
安琪和院长决定在元旦订婚了,订婚宴席决定放在元旦那天的中午举行。
前一晚上,安琪避开纷纷来祝贺的亲友,躲在房间里。由院长和父母承揽了一切事务,她只想静静地独自呆一会,甚至把房间里的电话也暂时拔掉了。
她心里溢满了幸福,甚至有点不能自制。这个挺拔、英俊、富有、能干的男人就要成为她的丈夫了,这是多少女人所梦寐的呀! 而现在安琪将堂而皇之地入住幸福皇宫!
过去的多少个日子,她一直漂泊和流浪,受欺侮和嘲弄,幸福对她来说,好象天边的云彩,可望而不可及。她的心灵,曾怎样地被阴暗和孤独,挤压得变形扭曲,痛苦麻木。她的生命曾象一条河,淤塞、死寂、发臭、干涸,没有歌声,没有阳光,没有绿草和鲜花。
后来,爸爸妈妈,用他们来自神的爱,让她的生命活泼、明亮起来,日日变化,年年不同。 而如今,一切要更加地缤纷灿烂了。因为人生爱情的明灯,已经点燃,上帝深藏在人类身上最洋溢的激情和最幸福的体验,将要爆发、喷涌。
人生,就象一束被发射到夜空的礼炮,将要彻底地燃烧,幸福的礼花四面喷射,飞霞如锦。 她给自己冲了一杯柠檬,在沙发上靠了靠,感觉脸蛋发烫,到镜子前一照,只见两腮通红,压倒桃花。 她盯着镜子中的自己,许久,许久、、、、、 在自己汪汪的两眼中读出深藏的失落和困惑。 她命令自己撩开氤氲在心湖上的幸福云彩,逼视自己隐而未现的内心。
她跪下来祷告。 突然嚎啕大哭。
祷告完,她迫不及待地拿出那叠半旧不新的稿子,在灯光下,翻开来,细细地品读。自院长走入她心灵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她没有与里面的男孩交流了。 在即将要成为别人新娘的时刻,她心里突然对他无限缱绻起来。 她盯着稿子上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连标点都不放过。一个个字迹,在眼前跳跃、整合,变成一活生生的男孩,从远方走来,推门而入,坐在她前面,带着孤独、忧伤,更带着迷茫中的信心和力量。
她轻柔地抚摸每一页稿子,忘情地闻那独特的味道,仿佛已听到他的心跳、呼吸、笑声和叹息。 冥冥中,她感觉他好象在等她,而她现在却要出嫁了。
如此想着,她伏在稿纸中泪流满面,痛哭不已! 这时,外面有敲门声,安琪慌忙擦去脸上的泪痕,迅速把稿纸塞在枕头底下,起身走到门口。
啊,亲爱的angel,怎么啦?你脸上、、、、、、院长推门进来,看见安琪的神情,伸手摸着她脸上的泪痕,盯着她红肿的眼睛,说,告诉我,为什么哭?
呃,哪里啊?谁哭了?大好日子,该欢喜才是,哭什么?才刚我开了点窗,不想外面一阵风刮进来,眼里跑进去什么东西,可把我难过得,就使命柔啊柔的。
安琪佯作平静,若无其事地边解释边请院长进来,招呼他坐下,倒茶,奉上,然后在他身边坐下。 蓓蒂好象也认出院长的特殊身份,尤其地热情兴奋,摇着尾巴,跑到院长脚边,乱抓乱咬。
咳,蓓蒂,你又淘了,别把裤子咬破。安琪弯弯腰抱起蓓蒂。 他喝茶,她坐在旁边陪着,两人突然不好意思起来,不知该说什么好。
许久,她说,这几天你辛苦了。 他笑笑,捋捋她的长发,搂过她肩膀说,应该的,我愿意。 她笑,他笑,心照不宣。 Angel,他把杯子放在茶几上,侧身捧着她的脸蛋,说,我看出来,你有心事。有什么不开心的事,你要告诉我,让我一起分担,知道吗?今天中午一过,我就是你的未婚夫了。
啊,没有呢,没有什么,别担心。安琪轻低头,脸贴着怀中的蓓蒂。 那就好。Angel,有一件事,我希望你能答应我。院长真诚地说。 什么事? 我想你在订婚宴席上送我两件礼物,这是我第一眼看到你时,就产生强烈的愿望想要的。他说完,脸上闪过几丝不安。
啊?她惊讶,抬起迷惑的大眼睛,注目他。 他黑黢黢的眼睛迎接她的注视,孩子般的单纯、天真和倔强,在一脸的刚毅和深深的城府中泛起,他一本正经地说,我想请诚森画你粗粗的辫子,和美丽的双脚。 粗辫子,美脚?这两概念又一次在安琪的心湖里击起千丈波澜。
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的办公桌下就压着两副辫子和美脚的画;公园小溪边他盯着她那双美脚的眼神; 他为什么对辫子和美脚如此终爱? 其实安琪曾经问过他这问题,他都保持沉默,现在依然。不过,这时安琪倒知道,原来诚森几次请求要画她的辫子和美脚,是为院长服务的。
没怎么想,安琪就同意了,院长安排她明天上午到诚森房间,在中午宴席开始之前就可以画成了。 元旦,整个城市沉浸在欢庆中,双喜临门的孤儿院就尤其热闹。孩子们放一天假,由保姆和老师带领出去玩了,院长忙着在前面安琪举行过生日晚会的宾馆里安排宴席的准备工作。几天来,该发的请贴都发完了,市里面头头脑脑的人物,生意场上的合作伙伴,差不多都要赴宴,因此院长忙得不可开交。
上午,安琪来到诚森画室,就是上次她进去钉扣子的那一间屋的半间,因为屋里有点凉,诚森就把画画的地点转移到他的寝室,就是挨着画室往里面的一间。很简单的房间,基本没什么摆设,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个折叠衣柜,有点凌乱,光线不太明亮,屋子角落烤着火。
诚森把画架摆放好,叫安琪坐端正,选好角度, 对着她上半身打开专门的灯光,先为她画辫子。 这时,安琪才真正领悟院长说的话,诚森确实是个画画的天才! 就在他那只画笔挥舞下,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安琪粗粗而精致的大辫子活生生地搬到了纸上。 诚森把画摊在床上招手安琪过去观看。
乍一看到,安琪失声大叫,脸色苍白,差点晕倒。 痛苦的记忆刹那如毒蛇咬痛心灵,她真切地怀疑自己的辫子又一次被绞下来了。 摸摸自己背后的长辫子,紧紧地抓住,她才确信,这是一副画。
看到安琪的反应,诚森惊呆了,慌忙给她倒了一杯水,服侍她坐下。看着她喝水,并且情绪平稳下来,诚森黝黑的大眼睛里露出不解、迷茫和神秘,又带着安慰和力量。
与他的目光相遇,她的心一下战栗了,好熟悉的眼神啊,在哪里见到过? 为掩盖自己的神思恍惚,她匆忙把视线转移开。 诚森看看表,还不到十点,就对安琪说,准备好了吗?现在就画你的美脚。赶点紧,十一点前能完工,正好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赶上十二点开始的宴席。
安琪点头同意,放下杯子,听从诚森的吩咐,脱了袜子,在一条竹藤长椅上躺下,把脚搁在一高凳上,诚森把灯光对准她的美脚,选取不同的角度,又舞动画笔画起来。 不时地两人闲聊几句。
大部分时间,诚森都全神贯注在他的画笔上。于是,安琪就转着眼珠,环顾这间小屋,尽目光所能及到处:天花板,是石灰简单粉刷后的毛胚;旁边的一扇窗户,湖着简单的墙纸,隐隐可以看到外面光秃秃的枝桠。对面的墙壁上,好象挂着一副放大的画,由于灯光暗淡,她得眯起眼睛仔细看。
看着,她皱起眉头,极力在记忆里搜索着什么。 不好意思,雪老师,你把脚稍稍往这边搁一搁。诚森擦了一把额头的汗,对安琪说,发现没有反应,就高声再说一遍,安琪猛惊醒,道歉,移移脚,眼光又在那副画上沉寂下去: 一条汹涌的大河,从山谷里奔腾出来,两边是高高而险峻的山脉。好象有巨大的风,把山上的树木吹得东倒西歪。河面漂着一只摇篮,隐约中看到里面躺着一糨褓中的婴孩,黑黑的皮肤,张着嘴巴,大哭,泪水象两根银线,在眼角抽出来。 安琪盯着画面,一动不动,内心波澜壮阔,澎湃翻滚。
许久,她对诚森说,那边挂着的画,我好象在在哪里见到过? 画?诚森顺着安琪手指的方向回头瞟一眼,说,哦,这副画、、、、、这是曾经得过大奖的作品,你见过不奇怪。 得奖?安琪略思索,睁大眼睛,惊讶地问,你能保证它是得奖作品? 诚森肯定地点头。
安琪扳着指头,略沉吟,问,可是在五年以前? 诚森停下手中的笔,略思索,点头道,五年以前,是,没错。你怎么知道得如此清楚呀? 惊喜在安琪眉梢跳跃,她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腾地坐了起来,急切地问诚森,别管我怎么知道,告诉我你怎么能肯定它是五年前的得奖作品?
对她的反应,诚森很意外,沉默一会,含蓄而肯定地说,我完全能肯定它就是。我很有点明白,雪老师,你何以对它那么感兴趣? 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安琪脸上闪过几丝失望,她也没有回答诚森的问话,两手交叉抱在胸前,一时沉默。
这时,张助理推门进来,问,你们还要多少时间完事? 诚森看看表,说,你跟院长说,十一点前保证完成。 那就好,你们忙。张助理特意用眼神跟安琪一声问候,关门走了。 诚森捋捋袖子,又拿起画笔,把灯光稍稍调了调,对安琪说,雪老师,那副画咱就先放一边吧,还是把本分的事先做好,别误中午你的喜宴。对了,趁机我得向你贺喜,你真是有福气的人,初恋就碰上这么优秀的男人。
安琪淡淡一笑,复躺下,道,谢谢。其实,你也是很优秀的人,坦白交代,你的梦中情人呢? 呵呵,被安琪一调侃,诚森憨厚地笑了,说,还梦中情人呢,我还不晓得恋爱是什么滋味呢?
啊,你还没有恋爱过? 嗯,如果暗恋算恋爱的话,那就有过。 安琪皱起眉头道,暗恋?那应该不算恋爱吧?如果那算,那我现在也不算初恋了。
安琪的话让诚森的心莫名地一慌乱,脸颊红了红,连忙把眼睛专注在画笔上,许久没说话。 过了好大一会儿,他停下手里的活,抹了抹额头的汗,冲着安琪笑着问,哦,呵呵,你暗恋过谁啊?谁有这么大魅力?真是幸福,让这么美丽的女孩暗恋。怕是他压根不知道,要是知道的话,肯定不会让你暗恋的。
哇,你好象突然领悟了。安琪的神色认真起来,说,跟你说实话,我确实在院长之前暗恋过一男孩。这、、、、、也是一直令我困惑的。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你知道我暗恋谁? 谁?诚森的心又一阵慌乱。
是、、、、、安琪手指指那副画,说,他极有可能是这副画的作者。这就是刚才我为什么对这副画感兴趣。 什么?诚森大惊,被雷轰一般,画笔从手中滑落。稍镇定,他弯腰拣起来,拿纸巾擦擦笔杆,低头又画起来,同时问安琪,你跟他,什么时候认识的?声音微微发颤。 安琪刹那沉郁下去。
许久,说,我还没有见过他一面。我是在他的自传稿子里认识他。
自传稿子?诚森提高了音量,画笔又一次从手中滑落。 怎么啦,你?安琪不解地望着他,说,你感兴趣?我就让你看看这自传稿子吧,就在我包里放着呢。
于是伸手从身边的凳子上取过包,拿出那一叠稿子,递给诚森。 诚森接过,打开,阅读起来,两手不住地颤抖。 他的心又回到了过去的年月,这是他在最痛苦的时刻写下来的: 我的自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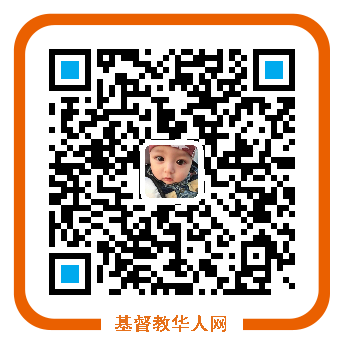
- 阅读排行
- 阿珥楠禾场的典故
- 你确定你不是心怀二意的人?
- 人生只有五天!好好珍惜过……
- 基督徒如何看待死亡
- 漫谈什么是幸福
- 我们所有的遭遇都有神的美意
- 最美的“保险公司”
- 成为时代的“巴拿巴”
- 友情、爱情、慰问和生日祝福语
- 撒该的故事
- 外面和里面
- 圣诞节中英文祝福语
- 禁止嘴唇的智慧
- 马丁路德小传
- 自负的船长
- 童话新篇之小玉如冰--遇见天使(续)
- 在地如同在天
- 生不带来,死要带去
- 不是审判而是拯救
- 孤单的木炭
- 关于“不许女人讲道”之我见
- 爱的那份痛
- 与神对话 :属灵的大麻风
- 基督徒为什么要聚会?
- 阿贝(短篇小说)
- 有钱时,人眼红你;没钱时,人瞧不起,怎么办?
- 恩典何奇异:从蒙羞(奴隶贩子)到蒙恩(教会牧师)
- 思想
- 那个呼唤他的声音
- 沙伦玫瑰第:初迈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