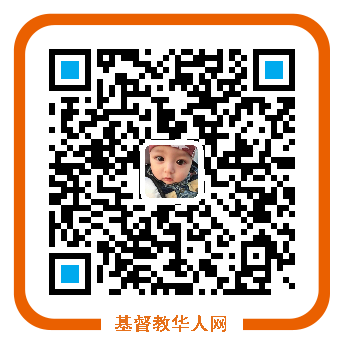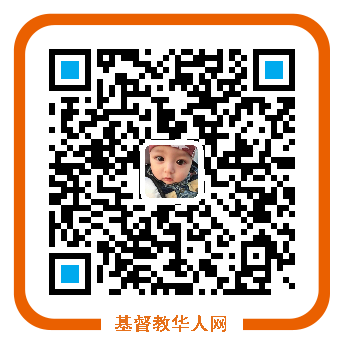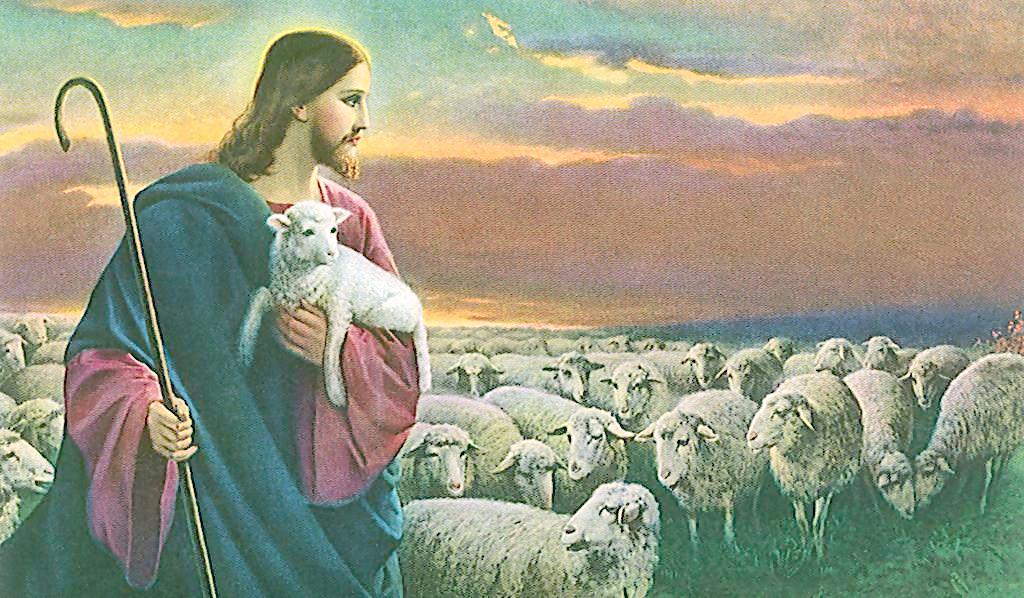我从中国大陆来美国留学已有四年,归入基督信仰神将近两年。回顾这四年的历程,无论在生活上、学术上和经济上都获得了在国内无法想象的收获,但最大的收获却在意料之外,就是让我找到了宇宙独一的真神,我的生命因此成了有源之水、有本之木。每当我环顾四周从大陆来求学工作的莘莘学人,在异国他乡为自己的生存空间和生命的价值辛苦拼搏时,常常会感慨万分,因为他们就是两年前盲目的我。 一、突破无神论的“神话” 我是在大陆绝对无神论的教育环境中长大的,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这种社会和家庭环境使我从小养成信奉理性、科学及自我努力的人生观。文革中,我下乡插队劳动将近六年,艰苦的环境更加深我万事靠己的坚定信念。后来我进入医学院和研究院,毕业后留校执教四年,于一九八六年来美国攻读博士学位。这些在信主之前,我都盲目地归功于我本人的刻苦努力,外加一些中国人常说的“运气”。 中国大陆的整个哲学体系是建立在×××主义的唯物论上。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绝对形而上学、属于唯心论的一切宗教都被认为是属于认识论的低级阶段,唯有×××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才进入了人类认识的高级阶段。尤其是我们这些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更认为真理是必须被证实和可重复的,因此听到有人谈论神时,我很自然地反应就是“(神的可证性)是什么?” 另外,在大陆这个奇特环境中长大的人,对信仰问题往往避而远之。我们经历过文革,在中国大陆这块绝对无神论的土地上,人们塑造了一个肉身之“神”,然后崇拜,最后摧毁。因此我当时认为,神是可以被人用各种方法塑造起来的。耶稣是个历史伟人,但他的神性可能也是被后人塑造的。 以上的这些观点实际上都没有摆脱十几年前唯物论的潜意识影响。 实际上,即使从科学角度来看,有心人也能觉察出无神论本身后面是“不可知论”。例如,目前最新的宇宙起源的科学假说认为,宇宙中各种星球的形成,是由于宇宙中心某些因素“偶然”相触爆炸而成,即宇宙大爆炸学说。这里本身就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这种“偶然性”在几亿年的宇宙进化史上,只发生仅有一次。各星球之间的引力维持得天衣无缝(因为地球离太阳稍近或稍远一点,人类不是被烧死就是被冻死)。难道这几亿年中,那个曾经引起宇宙形成的“偶然因素”再也没有出现过?有趣的是,万有引力发现者牛顿晚年只崇拜一本书──《圣经》。其实《圣经》中提到神第一天造“光”,而人类的理性认为是“大爆炸”。 我是研究医学遗传学的,人类起源的科学假说目前是建立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基础上。我学过并在课堂上讲过进化论,进化论本身至少有两个问题至今不能自圆其说:一是第一个细胞的起源;二是生物进化链中中间环节在考古上的缺失。众所周知,人的尸体最后还原成土,其实《圣经》中提到神没有用水或空气造人,而是用泥土造人。 茫茫大千世界,科学往往只能解决如何(How)?只有神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Why)?我逐渐意识到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竟建立在自认为有扎实根基的科学定理而实际是脆弱的假设上,这种有色眼镜本身是一种限制。 以前我认为,基督徒是好人,但他们大概因缺乏自信和性格心理失衡而去追求一种超然的精神寄托。做学生时,我很崇拜爱因斯坦,他精辟的相对论简直是集中表达人类智慧的高度结晶。爱因斯坦在他发现了相对论后,他的眼睛也转向了神;孔子所唯一崇拜的中国“奇哲”老子,两千多年前就曾在他的名著《道德经》中写道:“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历届美国总统中有不少是虔诚的基督徒,美国前总统杰克逊就曾说过,美国的立国基础是《圣经》。 古今中外这些性格和智慧超人的巨匠,都将自己的生命信仰不约而同地投向这位宇宙本体设计师,这使我开始对原来所执着的无神论的“完美性”和“终极性”产生了怀疑,并且对宇宙和生命的“神性”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进行了探讨。因为声称宇宙中有一位真神,或者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谎言,或者就是一个被人类智慧和理性所能测透的最大的宇宙奥秘。今天的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答案是后者。 其实,在一般的无神论环境中,人们也常提到“运气”。“运气”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它概括了自身努力之外所有超自然力量的总合。“运气”是随机的吗?“运气”的重复性和可证性怎样?等等,人们可以对“运气”提出类似对神发难的几百个问题,但却很少有人去探讨“运气”后面是什么,象原来的我一样,却默默地无意识地接受了这个非科学的神话。 二、基督教文化的吸引力 促使我对基督探讨的另一个因素是基督教文化的吸引力。基督教在人类文明史上起过巨大作用,整个西方的文化是与基督教不可分割的。来美国之前,我在西欧做过研究工作一年,参观过西欧不少名胜古迹。巴黎罗浮宫的许多世界名画根本上就是描写《圣经》中的故事;西方社会中的自由、平等和人权的概念也是建立在人是神的杰出创造这一基本的概念之上的。西方的绘画、雕刻、音乐、建筑、哲学、文学、政治等都有着强烈的基督教背景。 因此,进入西方社会,我当时认为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认同西方文化。要了解,自己必须同西方人打交道,才能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文化本源。 在我就读的大学附近,有一个中国人的基督教团契,他们由来美十几年的中年知识分子家庭组成,每周五晚上聚会查经。当时我想我的英语水平还不够达到与美国人深谈宗教哲理,必须先与中国人互相探讨,所以我们夫妻俩都参加了这种聚会。 在查经聚会中,也逐渐了解到这群虔诚的基督徒,不是象我以前所认为的“雷锋式”的乖孩子,他们有追求和探讨,最大的特点是他们有一颗真诚的爱心,使我们这些在大陆环境成长起来、高筑城府而性格扭曲的人,看到了人性最宝贵最真实的真善美的另一面。他们不但耐心地帮助我们了解《圣经》和基督教,而且还在生活上帮助我们度过了大陆学生在异国他乡求学最困难的第一年。今天我回想起来,才开始理解当初来美后幸运地遇到这样一个基督徒团契的“偶然性”的本源。 基督徒整个信仰的根基是《圣经》,我原来也对《圣经》感兴趣,只是从理性和求知的角度。《圣经》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翻译语种最多的一本奇书,单就《圣经》的文学、哲学、历史、艺术等方面的文化价值,都是无与伦比的。当时我想,作为一个现代文明人,生活在西方文明社会,若不了解《圣经》,知识层面会少一大截。 刚开始读《圣经》时,对《圣经》中的神迹、创世、死里复活、医病赶鬼都不太理解,甚至反感,认为降低了《圣经》本身的价值。后来才慢慢领悟到,《圣经》是创造人的神对被创造的人的启示,根本高于被创造者的理性;若被理性和逻辑作茧自缚,很难了解《圣经》的真谛。《圣经》有其准确的预言性,我是学医的,一千多年前的新约圣经中,就提到男性同性恋者将会发生一种近年来才刚刚发现的AIDS病(罗1:27);再如,三、四千年前的旧约圣经记载,神要以色列的男孩第八天行割礼(割包皮)。医学上任何手术都要解决两大问题:止痛和止血。几千年前在荒漠的中东地区开始的这个犹太人的传统竟然维持到今天。今天的医学研究才刚刚发现,男孩在出生后第八天时,阴茎包皮上神经末稍还未形成(无痛觉),而血液中的凝血酶原浓度在出生后第八天达到一生中的最高峰(止血)。其实,圣经中有许多类似的预言,有些已经被证实,有些还在实现中(有许多专著介绍,这里不一一引用)。这些预言常常使我震惊,它跨越了漫长的时间和辽阔的空间并具有相当的准确性和专一性。这种预言不可能来自巧合或人类智慧的逻辑推理,只能来自神的启示。 问题一个个地被解决,我垒筑的信仰障碍一个一个自破,云雾逐渐消散,下一步就是自然而然地投入,一九八八年,我们夫妻同时接受了人类理性永远无法理解的这位救主。 三、基督信仰的生命价值 两年的基督信仰,使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根本的变化。当我夜深人静独对星空时,我觉得自己迷惘的生命有了归宿,以前偶有的那种对生命终结的恐惧感也消失了,在异国他乡。前面道路虽然困难重重,但我的生命深处有一种很难表达的方向感。因为我知道,我已经将短暂的有限融合进了宇宙之无限中去了,与神发生了一种关系。现在我在理解孔子当时那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心情。 除了赐给我这种无价的内在平安喜乐感外,这位真神在我们家庭生活、工作学习环境中暗暗地显示出他的信实和大能,我也亲身体验到我以前一直认为幼稚可笑的向神祷告的巨大奥秘,这种基督信仰比起大陆当时的那种盲目的唯物主义信仰来,简直是天壤之别:前者是一种生命;后者充其量不过是一种理想。 以前,我认为基督徒生活是多么可笑,但现在要说,非基督徒生活是多么可惜! 我愿意真诚地向神祈求,求主耶稣的圣灵进入到每一颗饥渴慕义的大陆学人心中。阿们! 作者来自上海,从事医学研究,现居美国华盛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