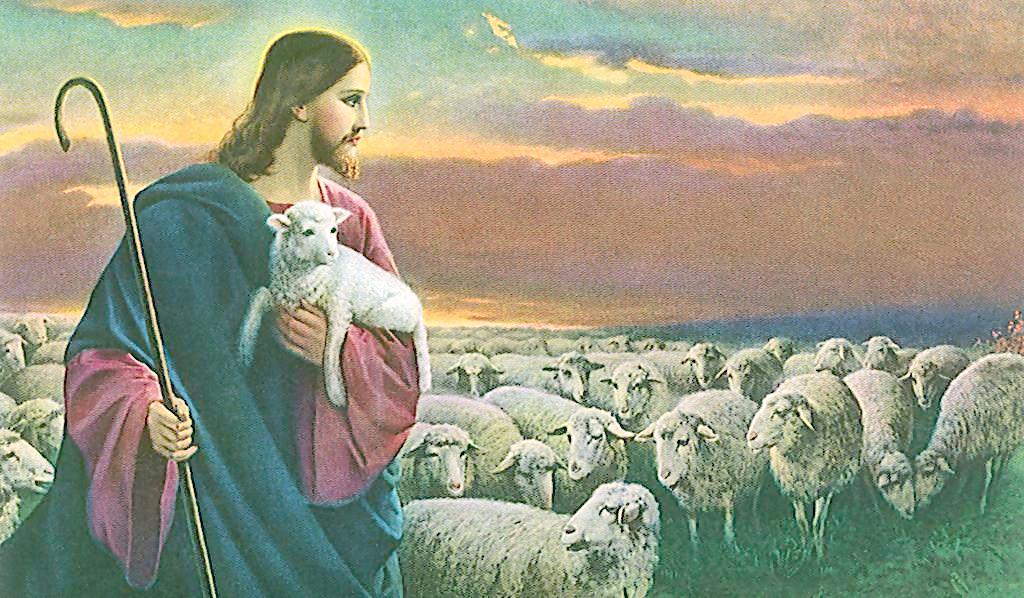|
新闻
国内
海外
社会
祷告 学习 进深 资源 文艺 诗歌 小品 笑话 |
福音
初信
讲章
资料
见证 科学信仰 疑难问答 音乐 小羊 赞美 天韵 |
舞蹈
广播剧
祷告吧
生活 感悟 妙语 心灵 圣经 在线圣经 圣经朗读 |
生活
恩典
亲子
婚姻
讲道 吴勇 宏洁 崇荣 教堂 每日灵粮 恩典365 |
在线祷告
欢迎投稿 在线查经 老版网站 奉献支持 基督书库 |

“红红的太阳下山啦!咿呀嘿呀嘿!成群的羊儿回家啦!咿呀嘿呀嘿!小小羊儿随着妈,有白有黑也有花,你们可曾吃饱啊。天色已暗啦!星星也亮啦!小小羊儿随着妈,不要怕,不要怕,我把灯火点着啦!呀嘿!呀嘿!呀嘿!”
当我决志时,就想起了这首儿时唱过的歌。小小羊儿回家了,牧师说我是失路羔羊,在羊圈外流离兜了一大圈,最后终于失路知返,归回天父的器量。
一、童年梦断
着实我十二岁就受洗为上帝教徒,今后六年,星期天的主日弥撒我很少缺席过,也在教会资助神父做一点服事的事变。神父送一本圣经给我,要我好好读,可是我总读不下去,创世记翻不了几页就憎恶了,想人类一开始怎么就有那很多的事端呢?看起来和当代人的纷骚动扰有什么差异呢?这本书那么厚,又那么无趣,不看也罢!因此在教会几年下来,对付圣经的相识也不外是几则耶稣说的故事罢了,我最耳熟能详的就是“荡子转头”和“穷未亡人的两个小钱”等等。我经常想荡子转头有爱他的父亲切情的拥抱,而我呢?有谁会包涵我,给我一个拥抱呢?
十一岁那年,我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我介入了一个世界性的音乐角逐(着实原本该我学长介入的,他临阵脱逃,便由我代表他出赛),筹备进场之前,先生正为我的琴调音,就在前台的与赛者将近演奏完毕时,“迸!”地一声,琴弦断了,我的心也随着绷紧了起来,先生固然慰藉我说: “没相关!没相关!顿时就可以装好!”然则,我整小我私人却仿佛不听使唤了似的,无法安静下来。虽然,那天的示意和泛泛差了许多,我本身也很惆怅。
原本,我是一个不怕上台的孩子,每次出去介入音乐角逐,我就很兴奋,由于既不必去上课,又可以出去玩,得不得名,对我也没多大的影响。但那一次差异,我的父亲和他独一的姐姐(我的姑妈是我父亲在台湾独一的亲人)都坐在台下,第一次听我拉琴。在这之前,父亲从来没有介入过我的任何角逐。我看到他扫兴乃至是絕望的心情,也看到姑妈带着慰藉的心情,我想他们必然认为我不外尔尔,不必再操心种植了。
其后我才知道父亲为什么那样扫兴,原本那次的角逐是最后一次以公费送小留门生出国深造的机遇。其时我的表哥、表姐都已出国读书,大表哥也是公费留学的优越门生。父亲虽然也等候我可以或许出国读书,可是没想到我的示意不外云云,扫兴之情天然不在话下。
跟着那一声弦断,我开始辞别本身的童年。不知道是幸照旧不幸?那一声弦断就像我生掷中的发蒙,以后我发明人生并不都是无忧无虑的,今后的二十年,我不太敢碰琴,仿佛我不再能演奏出好的音乐了。
二、“失败”是我的注册商标
这件事压在我内心,就像一条冬眠的毒蛇一样,每当我神色舒畅的时辰,它就从我心底钻出来,讥笑我:“你兴奋个什么劲儿?你是个失败者!”“失败”仿佛成了我的注册商标,跬步不离地随着我;我到哪儿,失败就跟到哪儿。它啮噬着我的快乐,我的芳华。于是,我爱上了秋日,由于那落叶的冷落,犹如我的心境。可以说我的童年就像炎天一样,金黄光辉灿烂,学音乐、学跳舞,天天都是无忧无虑的,但此刻却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上了中学往后,一方面家里弟妹浩瀚(我是老大),袓父又三天两端住院,父亲只是一公事员,承担极重,就实行经商赚钱。但几年下来,他的买卖仿佛只有第一回合是赚钱的,接下来就要赔钱,最后父亲只好提早退休,以退休金还债、还袓父的医药费。我本身也从国中开始一向到大学结业,每年的寒暑假大多在打工中度过,我做过各式百般的事变,卖鞋子、倾销杂志、卖早点、排除衡宇、幼儿园助理先生,百货店陈列员等等。但我并不觉得苦,也从未诉苦,心中总有一个光亮的设法,等候来日诰日的太阳仍旧光辉灿烂升起,但愿就在来日诰日!
就在这种对将来布满但愿、又在当下感觉到失败的情感中,我度过了难挨的六年中学糊口。六年里,我固然上教堂,也介入不少教会勾当,却谈不上有很大的感觉或打动,更谈不上安全与喜乐。就是向神父告解,也经常得想个老半天,委偏言出几个芝麻绿豆的事端来怨恨——一方面是认为本身没什么罪,一方面首要由于“心”是麻痹的。
尽量云云,我心底仍有一个渴望,渴望考上大学可以让父亲对我昔时没拉好琴的神色获得体贴。于是我把联考志愿表全填上了法令系,同心用心想在将来当个好法官,灿烂门楣。没想到联考发榜,我竟以0.75不到一分之差落榜,固然在夜间部大学联考中考上东吴法令系,方圆的亲朋也以为这是个勤学校,更有优越的法令系传授,但失败情结仍旧像乌云一样覆盖在我心头,一分一秒都扎心刺痛。我知道只要我改考文组,那早就上榜了,只是我到底要姑息考上就好,照旧要按着我的志愿走呢?我选择了后者,只好包袱失败的疾苦。
年青的我,独自离家北上读书,我的精力支柱来自学校的学姐、学长及同窗们,他们都很照顾我、疼我,奇怪人的糊口天然也是多彩多姿,我也能融入课程的爱好中。但经常那漫长的白昼,就在孤傲不语中度过。直到有一次周未回家省亲,饭桌上父亲沉默沉静不语,如有所思。我问他怎么回事,父亲溘然表情一变,手指着左前线说:“那XXX也考上了大学!”我一想,他指的偏向是我们的邻人,他们的侄子正是那一年在我们宿舍区里独一考上白天部的。我的心一沉,回到学校后再也无法用心上课,最后只好休学筹备重考。
重考的日子,使我的日子越发惨淡,更为难得,我寄住在同窗家,白日他们都出门了,我把本身关在房子里,把全天下弃在表面。有一天,我把书摊在桌上,心思却漫无方针的流窜,顺手在一张纸上埠孟地写着写着,不知道过了多久,待我醒转返来一看,“哀莫大于心死”、“哀莫大于心 死”、“哀莫大于心死”……竟写了满满一张!无情的煎熬却教我死命也要考上白天部大学。
三、由你“荒”四年
终于,我考上了白天部大学,但并不是我想要的科系。重做奇怪人,学长说“大学”就是“由你玩四年”(university),我比如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小鸟,一旦飞到了一个辽阔的天地,却又不知道要飞往那边去。我把教会丢在脑后,试图探求本身的人买卖义,上教堂就只在回乡时去应个卯罢了。
外表看来,我像一个康健宝宝一样,又蹦又跳,在社团里和各人疯成一团,私底下的我仍锁在自我的象牙塔里。于是,我把本身的情绪请托在舞台上,在哪里我随便地称赞、随便地表演戏里的脚色,由于我不敢演我本身,深怕人一相识我,就把我懦弱的“坚定盾牌”给戮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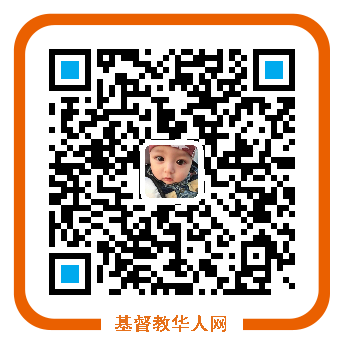
- 阅读排行
- 一个真实的婚姻见证
- 远牧师:蒙恩归主见证
- 倪柝声弟兄----生平简史
- 天堂、地狱的活见证
- 《神州》的感恩见证-远牧师
- 上帝的恩典大过人的软弱
- 刘王爱君的见证:姊妹的学习
- 寻找与叩门
- 四大爷的奇迹见证
- 我的得救见证
- 蒙恩见证
- 修迦南:他在四川地震救人时遇到温总理并聊起了福音(
- 比张海迪病情还要严重的孩子被神医好了
- 一个软弱肢体的见证
- “九代奇恩”与今天的中国教会
- 小草诗歌的作者:林英姊妹生命见证
- 见证:亲历5.12汶川大地震
- 歌星蔡琴信主耶稣见证(视频)
- 唐崇荣博士蒙恩见证
- 永恒长明:用福音原创诗歌感恩
- 神的慈爱永远长存
- 一次震撼人心的祷告会
- 信仰见证
- 奇异恩典---一位在香港中大研究院就读的内地学生信主
- 见证:神大能奇妙的双手
- 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散发基督馨香的女人
- 小敏姊妹:神的灵感动我高歌
- 十字架的路—灵性成长的秘诀
- 走出外遇 摘下面具
- 主为我钉十架,我为主做什么?